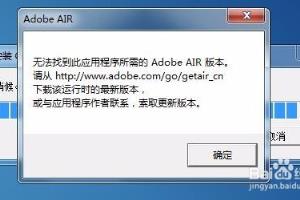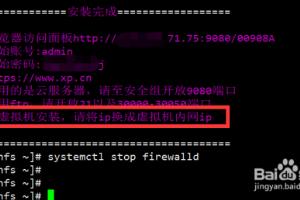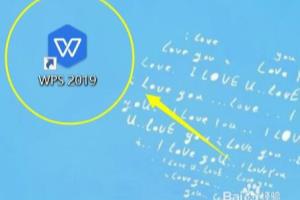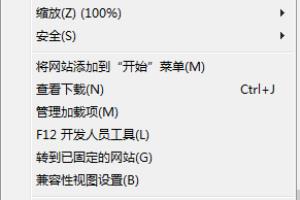最近严重拖住进度的,是溥仪的我的前半生这本书。百科的资料,永远是别人嚼过的口香糖。虽然同样有误读的风险,但文史资料本身,才是可以依赖的实证。至于为什么这本书会被用到,明天更新大家也就都知道了。我在此不多做赘述,只说这本书。
这本书根本就不是一本书,作者也不是一个作者。其中牵涉到几件大事。
首先要厘清的是重名问题。除了溥仪之外,亦舒以及其他作家,也喜欢拿这个名字,命名他们的自传或其他作品。这是第一个重名。第二个重名是,溥仪自己这本书上,其实有两个文辞风格完全不同的主要类型。
豆瓣读书对溥仪我的前半生的各版本有非常详细的描述。这个描述,点开一本溥仪的我的前半生的主要版本,就能在内容简介下看到。我把它附在文末,以防不测。这个简介的时间线很清楚,但实际其版本差异描述是不具体的。这书是一本每过几年都会再版的畅销书,其版本问题应该非常复杂。很幸运的,我这边本地的图书馆几乎收藏了全部有代表性的版本。但是这书显然还有不对的地方。在我两个月前第一次查询的时候,它的所有开架阅览副本已经消失了。我还因为多要了几个版本,触动了典藏资料室的管理。在最多调用五册并必须在阅览室阅读不可外借的苛刻条件下,我又被专门要求每次只允许取用两册。这种谜之限制没有最终深刻阻碍我的探究,这是当日当班的图书管理员对我的仁慈。
闲话到此,现专门说版本一事。从我拿到的七个版本来看,这书的版本主要分成四大类。
64年版和网传txt版是同类的,称为定稿本。这个版本使用了灰皮本为底本。在与灰皮本不同的内容上,其语言朴实,用词平淡,陈述和引用详实,有近现代学者著作的口吻。定稿版和灰皮本的目录设置逻辑,有一定程度的差异。我区分定稿版的标记,是当前版本是否有【罗振玉的努力】这一个小章目。有【罗振玉的努力】的,接近定稿版;没有这一小章目的,是灰皮本。与灰皮本相比,定稿本行文中,更正了大量的“讹误”,并以访谈记录和物证极大程度的充实了灰皮版文稿。这个版本的写作者主要是溥仪和李文达两个人,另外还包括了一个松散的,作用于访谈寻证的,包括史实相关人,编辑,学者等的一个顾问团队。
13年批校版和18年北京联合出版社全本(后文简称为18年版)是同一类,我称其为过度版本。这一类版本是九改九校时期的产物。其表现出定稿本的文辞特色,但在文字上与定稿本多有出入。这个版本产生的过程中,经历了几次印刷,和溥仪批改修正。其目录与灰皮本和定稿本都不相同。仍以【罗振玉的努力】这一个章目为例。过度版本中,这一小章目是第四章的第三小节;在定稿本中,它是第四章的第一小节。
文字上的出入比较明显的一处,仍在这一小章,是有关天津张园是八楼八底,还是七楼七底。我第一次拿到的版本是18年版。13年批校版和它一样,写的是七楼七底,于是被我归类到一起。当时我读到这,发现这个事,觉得很不可思议。华夏避讳四和七。如果能够建成七,一般会取六或者八。如果非要取七,多会强调是北斗七星的七,或者别的重要典故。我后来再看到的定稿本,写的都是八楼八底。这八个楼,是张彪为他的八个儿子,在张园后面建的,叫做宏济里。现在改写成鸿记里了。我拿到的60年版灰皮本的上册(下册缺失),不包括这一章,难以对证。11年版灰皮本根本就没有说张园几楼几底面积多大这部分内容。之后的版本添上这七七八八,又有版本点改,很有学者的风骨。这大约说明从确定灰皮本,到成书定稿本,其中有一个漫长的,文史专业化的编辑过程。
最后一类版本是全本,我拿到的是群众出版社的07年红皮全本(后文简称为07年全本)。这是一个再编辑版本,是群众出版社的一次尝试。64年版正式出版时,书中相关人物仍有很多在世。为限制不良影响,64年版对原书稿进行了大刀阔斧的删减。比如有关李玉琴的章节,第十章第四节离婚,被完全裁去。07年全本通过对比两个原稿本和定本,将这一节9页内容完全补正,并且补正了很多其他内容。
另外,60年版和64年版两个版本,是繁体字版。后来的近代成书才是简化字版本。现在的各家百科,多对此书有直接引用。
第二是作者问题。这个主要牵涉到灰皮本和定稿本,其他版本都是这两版的衍生。上文也提到,灰皮本是溥仪主要在溥杰的帮助下完成的,定稿本是溥仪主要在李文达的帮助下完成的。本来写书就是苦役。溥仪这种身份,有人代他执笔也是理所应当的。问题出在著作权上。
在研究这书著作权的时候,我发现这书的著作财产权保护期,已经于2017年12月31日截止了。这一条最终推动我将手上的文稿贴上来,开始复更。
db对我的前半生的版本解释
【《我的前半生(批校本)》以《我的前半生(全本)》为底稿,对溥仪在《我的前半生》清样上百余处批校意见进行工整理,配原稿照片和整理文字,真实反映了溥仪当时的思想动态和《我的前半生》的成稿过程。
作者从自己的家庭背景写起,回顾了他在入宫做了皇帝、遭遇辛亥革命、清帝退位、民国成立、北洋军阀混战、出宫、客寓天津、做满洲国皇帝、逃亡,直至解放后接受改造,成为普通公民的全部历史。他的写作即是个人的历史书写,也由于他的特殊的历史地位,全方位地再现了20世纪上半期中国社会所发生的历史变迁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