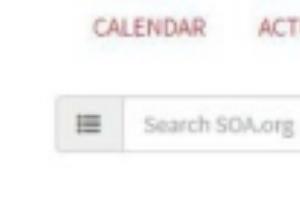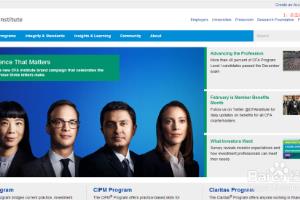唐诗宋词,被誉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之一,以至于千年后的今天,作为一个中国人,不说张口就来,但背出几首脍炙人口的诗词并不算难事,从中可见唐诗宋词的影响之大之深远。

我们在回味经典之余,往往会发现以诗文明的唐朝,作为创作者的诗人却大多仕途不顺,更不要说位列宰相之类的高官了,反倒是宋朝官员中,大多都很有诗词造诣。是什么造成了这样的结果呢?下面船夫带大家来寻找下答案。
科举制度出现于隋朝,唐承隋制,进而也让科举制度迅速发展,但与人们熟悉的科举考试不同,最开始的科举试题以明经为主,所谓明经,最开始是指诸子百家的学说要义,但自从汉武帝颁布“罢黜百家,独尊儒术”以后,再次提到明经,指的就主要是孔子教育弟子所用的课本:《诗》、《书》、《礼》、《乐》、《易》、《春秋》,后续各个朝代有过变动和分拆,但大体内容并未变化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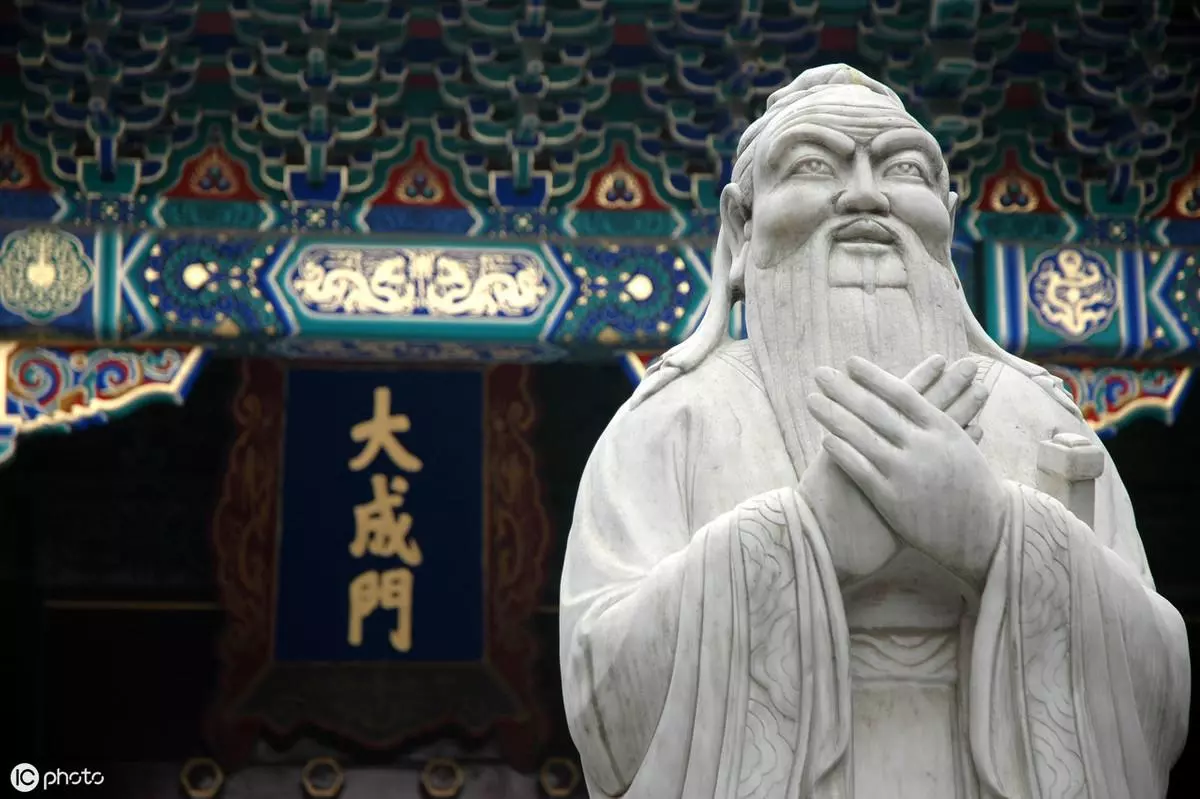
从中我们可以看出,当初孔子教学生时,是以重经义为主的,至于诗词,只是众多课程中一门而已。况且这里的《诗》,指的是《诗经》,其中大都为古体诗,与发扬于唐代的律诗和绝句有不小的差别。
唐朝初年重经义轻诗词的风气,我们可以从唐代封演所撰写的《封氏闻见记》中的一则故事,管窥全貌。
冀州进士张昌龄、王公瑾并文辞俊楚,声振京邑。师旦考其文策为下等,举朝不知所以。及奏等第,太宗怪无昌龄等名,问师旦。师旦曰:‘此辈诚有词华,然其体轻薄,文章浮艳,必不成令器。臣擢之,恐后生仿效,有变陛下风俗。’上深然之
上文中的师旦,全名王师旦,在唐太宗贞观二十年时任考功员外郎,负责主持科举考试,在对张昌龄、王公瑾二人进行判卷时,有意将其打了低分,要知道在当时张王二人素以文章诗词华美著称于世,对于这个结果连唐太宗都感到诧异,于是王师旦解释道:“这些人虽然文章写得漂亮,但实干能力不强,如果不打压,甚至养成只重视文章华丽的社会风气,就不好啦!”这个观点也得到了唐太宗的认可。
这也解释了为何文章诗词都很厉害的“初唐四杰”(见注释1),他们的仕途大都很不如意。
唐朝初期以经义为主的科举考试,的确为唐朝筛选出来很多优秀的国家公务人员,为唐朝的政治、经济和文化发展做出了很大贡献。但对于中国人来说,一旦一项事务和非常大的利益挂钩,就会吸引来众多“专家学者”来研究出相应的考试辅导资料。越来越多的考生不再用心钻研经义的真正精华,而是开始“走捷径”!唐高宗永隆二年八月颁布的《条流明经进士诏》,就提到了此问题的严重性。
学者立身之本,文者经国之资,岂可假以虚名,必须征其实效。如闻明经射策,不读正经,抄撮义条,才有数卷。进士不寻史传,惟读旧策,共相模拟,本无实才。
这里的义条,就相当于如今的高考英语常用词,文史考纲重点等等。正是有了这些所谓的考试辅导资料,让学生只追求明面上的考试效率,忽略了学习经义,忽略了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儒家学说初衷。

正是因为如此,一代女皇武则天在一次由其亲自主持的抡才大典中,临时起意取消了原本的经义考试题目,取而代之的是让入选的人们当场进行诗词创作。这一变招打的那些本已为胜券在握的考生们一个措手不及,某种程度上的确起到了很好的筛选效果,但自此也开启了唐朝中后期,重视诗词的科举潮流。
武则天之后,唐朝政权再次回归到李氏手中,在一些列的政变后,由唐玄宗李隆基将帝国带到了开元盛世。在这一时期,在科举取士中,诗赋的重要性逐渐高过了经义,唐朝时期的古文运动先驱独孤及(见注释2)总结道:
天下无兵百二十余载,缙绅之徒用文章为耕耘,登高不能赋者,童子大笑
从中我们可以得知,在太平盛世的大环境中,人们对诗赋的喜好很大程度上左右了其在科举中的重要性。最明显的例子就是朝堂核心高官的学问背景,在武则天时期,是长于吏务经义的狄仁杰。到了唐玄宗李隆基时期,则是长于诗赋的张九龄。

在唐朝刘肃(见注释3)所编写的《大唐新语》中记载了这样的故事:
武则天问:“朕要一好汉使,有乎?”
仁杰答曰:“臣料陛下若求文章资历,则今之宰臣李峤、苏味道,亦足为之使矣。岂非文士龌龊,思大才用之,以成天下之务者乎?”
从这段话中,我们可以了解,在长于经义的狄仁杰眼中,长于诗赋辞藻的文士大都上不得台面,往往都是说的好听,实干起来一团糟。但到了唐玄宗时期,被誉为“文场之元帅”张九龄出任丞相。新官上任三把火,掌握权利的他一方面提拔长于诗赋的后进人士,另一方面又排斥长于经义真的考生。
十年河东十年河西,当初盛极一时的经义,在与诗赋和竞争中败下阵来。这也是为何唐朝初期,诗人往往仕途不顺,但中后期很多诗人都当了高官。
注释1:“初唐四杰”指的是唐朝初年的王勃、杨炯、卢照邻、骆宾王四人,简称“王杨卢骆”。四杰齐名,原并非指其诗文,而主要指骈文和赋而言。
注释2:独孤及(725~777年),字至之,洛阳(今河南洛阳)人。唐朝大臣、散文家。唐天宝十三年,举高第,补华阴县尉。唐代宗召为左拾遗,改太常博士。
注释3:刘肃,唐宪宗元和末前后在世,曾任为江都主簿。刘肃收集唐朝初年——唐代宗李豫间的轶文旧事,编为《大唐新语》三卷,传于后世。